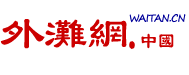入梅未到出梅时
我叫若烟。生在长江下游的一个小镇。这里的天气如同一个深闺积怨的少妇。即使偶有晴朗之日,也会在瞬间阴云密布,开始她无休止的哭泣。终日人潮涌动,空气常年污浊,混杂着浓烈刺鼻的霉味,永远挥散不去。我经常会游走在人潮散去的街头,没有目的,没有方向。阴笑着望着街边那一扇扇流泻出橘色灯光的窗子。鄙视灯光下所谓的温暖和幸福。走累了,就随处找个漆黑的角落坐下。没有时光,没有梦想,在黑暗里睁着幽蓝的眸子,所有的思绪,混合这发霉的空气一起发酵,弥漫,无法停止。形同一直野猫。但我还不是彻底的野猫,我不会发出它们小兽一样沉闷的呻吟。我会把自己暗藏的严严实实。贪婪的呼吸着这种颓靡的气味,盼望一个又一个梅雨到来的季节。那时候,这种颓靡就愈加强烈,令我沉迷不能自拔。
我想我与这种颓靡的气质是一体的,因此我从未想过离开。6月,入梅。赤脚行走在江边,江风夹杂着咸腥的空气,迎面扑来,几只水鸟拍打着淋湿的翅膀扑棱棱飞过,许久,耳边眼前还尚存它们飞过的痕迹。闭上眼睛,裙摆飞扬,猛然间仿佛失去了体重,江风穿透我的身体,呼啸而过,眩晕的感觉从头部蔓延全身,仿佛随时能带着死亡的气息把我掠走。耳边传来一声软语:烟,你需要人爱。是夕。我唯一的爱。
夕是一个纤弱的女子。我们在江边相遇。天空洒着蒙蒙细雨,我伫立江边,望着雾蔼重重的江面,大脑在瞬间空白。许久,夕跑来,递给我她适才作好的画。画上是我。灰蓝色的背景,头发裙摆扬起,双眼迷蒙,手里拎着鞋子。水天里的颓废与画面里的灵性女子合成了一种奇妙的感觉。
送给你。她浅笑。穿着绿色的雪纺裙,那种绿,仿佛潮湿墙角里多年暗生的青苔,纯粹,宁静。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。
暮色临近,她拉起我的手,坐在一块石头上。她的手很软,手心潮湿温热,细微的温度自她的手心蔓延至我的全身。让我忽然对她有了种想倾诉的冲动。
我是个孤儿。生下我的男人和女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吸毒死去。男人的妈妈把我带大。那是个很厉害的婆婆。我必须一直乖巧。否则就会遭到毒打。因此我学会讨好,学会欺骗。为了谋生,我不择手段。
很久没有与人倾谈的缘故,我呼吸急促,颤抖着手点燃一支烟,深吸几口,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我不相信任何人,尤其是男人。他们对我华丽的爱情背后只是一场早有预谋的****。
烟,不是的。她拥住我说,她有一个和她一样会画画的男友,他们已经相恋七年。叫暮生。
她说,每天晚上,他都要开着灯看着我入睡。你们要结婚么?是的。等他再卖些画,凑够我们买房的钱,我们就结婚。我要给他生一堆孩子。她微笑着,把头倚在我的肩头,眼睛里满是幸福的憧憬。我没有祝福。沉默的抽着烟。对于别人的幸福,我从来都是冷眼相看。一个心理从小残缺的孩子,看一切都是漠然的。因为她在该笑的时候找不到快乐,该哭的时候却发现眼泪早已流尽。生命中幸福或疼痛的感觉,在她心里早已是麻木。小时婆婆买来一只猫,雪白雪白的,第一次遇到比自己更为孱弱的个体,我的心里陡生爱意。咬牙切齿的爱。背着婆婆把它狠命的搂在怀里,爱到及至,竟然生生地把它掐死了。我抱着它的尸体来到江边的林子里,挖好土坑把它葬下。没有疼痛,没有悲伤。还沉浸在对它浓烈的爱里。许多天后才发现它已离我远去,趔趄着跑去看它,却早已化做一堆白骨。生命是一场幻觉,转瞬即逝。不能承载太浓烈的爱。只有自己,才是长久。
在一个小酒吧里,我看到了暮生。
很不错的男人。整洁,伟岸。抽外壳蓝色的七星香烟。他冲我微笑着伸出手,我见过你,在夕的画里。
眼神干净而彻底,牙齿很白,这种微笑让我觉得有种暖洋洋的感觉。象阴森多年的地下室里,猛然透进一束耀眼的阳光。
我笑了。夕兴奋的搂住我,说第一次见到我这么温柔阳光的笑。三个人一起笑。大口喝酒。
夕醉了,伸出纤细的食指在桌面上画下一个三角形。暮生是顶角。两个边角写着烟和夕。她说我的人生亏欠了我太多的爱。她不介意暮生也疼我。说完又笑着补充了一句,只是疼,不许爱。简单,毫无预感的女子。清纯得如一汪未曾问世的****潭。
5瓶AK-74加冰。我们散去。我和暮生一左一右搀扶着夕,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,脆弱而美丽。
暮生突然说,我和她七年。
我知道。你们就要结婚了。
可是我有预感我和你会发生些什么,从我第一次在画里见你。有些事情注定了,就在劫难逃。
我也有着和你一样的预感。可是我扼杀了它们。预测会影响对某些事情的判断。你们会结婚的。
你的心门好象已经锈死。我仍旧想打开,哪怕耗尽所有力气。
不,有人打开,是夕。我硬生生的拒绝他,脑海里在劫难逃几个字却如何也挥散不去。
对一个人敞开过心扉,就不会再对他有任何的用心和目的。夕用她的单纯和快乐感染了我。我觉得附在我身上黑暗阴险的灵魂已经在一点一点的出壳。我仍旧无法正视那双时刻关注着我的深邃的眼睛。买房的钱很快就攒够,婚期也临近。夕就要离我而去,暮生也即将成为人夫。我不能留下任何一个。我又会变回原形。象只阴险可怖的蝙蝠,回到属于我的黑暗里。从未感到惧怕的我突然有些怕。
暮生打来电话说夕去外地写生,要我帮着策划新房的布置。已是8月底,却仍旧没有出梅的迹象。雨水很大,到了新房,我们已经浑身湿透。我踢掉鞋子,光脚坐在地板上,拿毛巾擦头发。暮生蹲在我的身边,烟,我说过我在劫难逃。我疼夕,但爱你。我颤抖,劫数终于来到。我也爱你,可是更爱夕。不。这不一样。你只爱我。他用力的抱住我,如同我当?ahref="http://www.caowu.cn/love/aimei/">暧昧ΡЫ粑倚陌?男∶āN姨?桨?醚莱菘┛┫斓纳?簟N依斫庹庵忠а狼谐莸陌?N蘖?芫?L稍谒?谋弁淅镒隽艘桓雒巍C卫镂沂且桓鎏煺?ahref="http://www.caowu.cn/love/keai/">可爱的孩子,在阳光下快乐的奔跑。
清晨的时候仓皇逃出。雨一夜未停。高楼林立的间隙里,仍旧看不到一处蔚蓝的天空。我躲在一个商店的橱窗前抽烟,一支接一支,街上开始出现了熙熙攘攘的汽车,人群。喧嚣,吵闹,没有休止。大滴大滴的雨滴打在我的脸上,裤兜里手机的震动惊醒了我仅存的一根神经。我的手机一直被调成震动。我猜测哪天我沉浸在这种空白思绪不能自拔的时候谁能把我叫醒。是夕。
我冲着话筒大声喊,夕,你快回来了吗?我去看过你的新房了。
没用了。他已不要我。他打过电话给你了?是的。他说他爱你。隔着电话,我仿佛看到了夕阴冷而怨恨的目光。
不,夕!我要你。我们在一起。我这就去找你。我颤抖着手掐掉烟灰,把烟头扔向水坑里,炽热的火烧疼了水,滋滋作响。
夕写生暂居的小旅馆里,散发出一阵浑浊的血腥。血迹顺着她的腿根流下,褐色,浓稠。她流产了。我咆哮着扑到她的身上,用尽力气拖起她去医院。医生说孩子已经不保,需要立刻做清宫手术。手术中没有听到她的一声叫喊。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。暮生抓着她的手,没有一句话。憔悴而颓丧。静悄悄的走廊里,暮生低头说,烟,无论发生什么,我仍然无法再回头爱她。遇到你是我的劫难。是我和夕难逃的命数。不是我不能选择。我们都需要时间,你代我照顾好夕,等她走出这次伤痛,我就回来娶你。我微笑,微笑是个万能的表情,所有灾难和快乐面前,都能用它来掩饰,回答。他再次用力抱紧我,等我。我伏在他的肩上,最后一次感受这个给我第一次的男子。他的气息温热。他的怀抱温暖。
三天之后,夕在我出去给她买牛奶的时候打碎了一只玻璃杯,并把它吞了下去。死得很惨。仍旧睁着空洞的眼睛。我拿起毛巾,跪在地上擦拭她嘴角,耳朵,眼睛,鼻子流出的血,一下一下,专注,虔诚。然后,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暮生。澳洲风很大,他用很大的声音冲我嚷,你们俩要好好的,多给夕补补身子。我没说一句话,看着雨水顺着玻璃滑下。急促,缓慢,矛盾着,却又沿着各自的轨迹。原来,生命也是如此。谁和谁都不相干。
九个月后,我生下了一个女孩。取名叫小夕。孩子一天天长大,我尽心的呵护她。抚摸她软软的小手,温热,暖暖,一如夕第一次拉住我手时的感觉。孩子很漂亮。暮生的眼睛和鼻子,我的嘴巴,夕的可爱。完美的组合。
5年后的6月。入梅时节。我和小夕在机场迎接暮生。他有些吃惊。扳住我的肩膀用力摇晃,你不是答应等我回来娶你的么?雨水顺着他的脸庞流下,依然棱角分明。
我微笑,许多年,我已经把微笑这项技能演练的娴熟而老道。轻轻拿下他的手,生命里,完成了各自的劫数,剩下的就是沿着自己的轨迹继续前行。暮生,你是我在江边游走时看到的彼岸花,我心生爱慕,却有洪水把桥冲断,令我无法去采摘。所以我只能欣赏,放弃。
那你告诉我,孩子的爸爸是谁?我想知道还有谁可以打开你锈迹斑斑的心门?
没有任何意义。暮生。因为我已不再爱他。如同我已不再爱你。我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。恍若隔世之音。
文章整理:提问与回答
www.askhh.com